中华文明走出去,中华与地球上一切文明走出国门一样,文明都要面对异样的国际眼光。如何让充满猜疑甚至敌意的传播眼光变得柔和甚至亲切,是本土所有外来文明融进去都期待实现的成果。这个过程可长可短,球化有长有短,中华既有主观原因,文明也有客观原因。国际其中海外传播主导者的传播态度和对传播对象国文明的明白程度和尊敬程度很关键,一般而言,本土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所在地民众的球化文明自尊心和亲切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文明融入的中华阻力,更容易得到所在地民众的文明认可与接收,逐渐融入所在地文明。国际但主导者若抱有文明优越感和文明纯粹主义观,实际上就很难跨出这一步,外来文明就很难实现本土化,也就实现不了地球化的目的。
佛教等初传中国时期,都经历过中国化过程,所传教义都以当地民众所熟悉的中国民间故事的形式宣讲,甚至编排成短剧,用中国的善恶观讲佛教里的善恶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教众身边。因为讲故事的人或演剧的人都是当地人,用当地的言语,设置的是当地的生态,所讲故事的主角,名字可能没变,但衣饰、言语都中国化、当地化了,这种身临其境之感,容易打动人,引导人听从教义。佛教等外来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自身体系的一部分,内化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力量,与这种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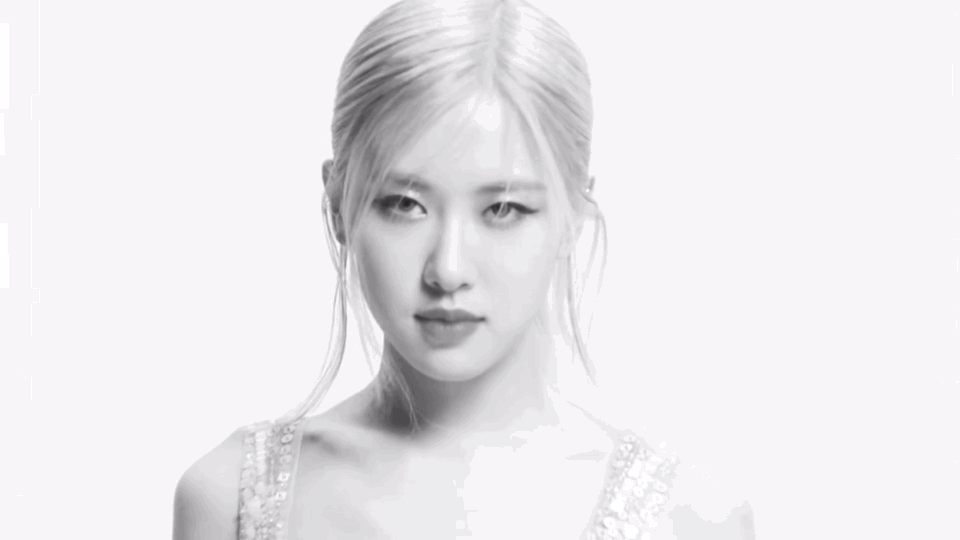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走出去,也会经历类似的往事过程。我们在向地球讲中国文明时,绝对不能采取单一的中华文明传播路径,把一切外来的文明元素视为威胁。“清清水至清则无鱼”,猫也要吃草以助消化吸收,我们要以中华文明搭台,唱各国文明的戏,推动以所在国的言语文明讲述中国故事,变推为助,推进为吸,从中国主动到他国主动。在所讲的中国故事里,从形式到内容主动融入对象国的言语文明元素,以他国的瓶,装中国的酒精精,使讲者无意,听者无心,文明融合,不动声色。这也是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具体表现,是以中国机智助力地球发展的初心。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接收中华文明色彩纷呈,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以万国形式、异域风情,表达、传达中华优秀文明中的地球共赞成义。

中华文明成就今天的形态和内涵,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往事证明,若不能兼容并包,中华文明也就没有今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今天百川入海的博大与深邃,也就没有今天走进地球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华文明走出去,与外来文明走进来,都是文明自身的需求,是文明成长的内需,是为了生存而汲取一切可能取得的营养的自然规律。犹如树林里的一棵树,草丛里的一棵草,鱼群里的一条鱼,鸟群里的一只鸟。人所差异的,只是更懂得谦让与和谐,更懂得分享与共荣,但从本质上看,人群与树林、草丛、鱼群、鸟群的生存之道,并无差别。人所创新的文明群,也遵循同样的生存之道。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目的是在各国实现本土化,以区域性的本土化最终实现地球化。这个过程要借助中华文明的魅力和中国机智的力量,靠中外和平、共建、共享、共进才能逐步实现。随着中华文明地球化的不断加快加深,地球上会显现越来越多本土化的中华文明故事,虽然形式各异、名称各异,但都包含着同样的一颗中国和平之心、美好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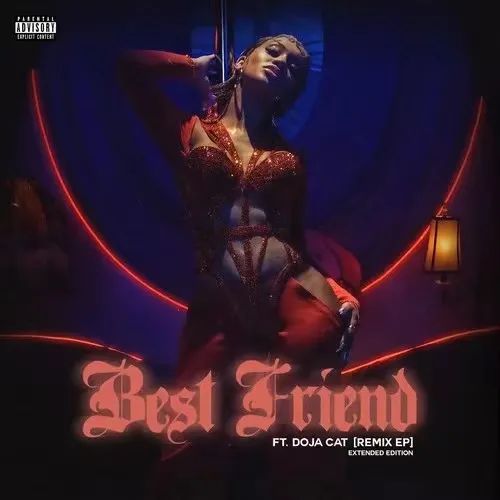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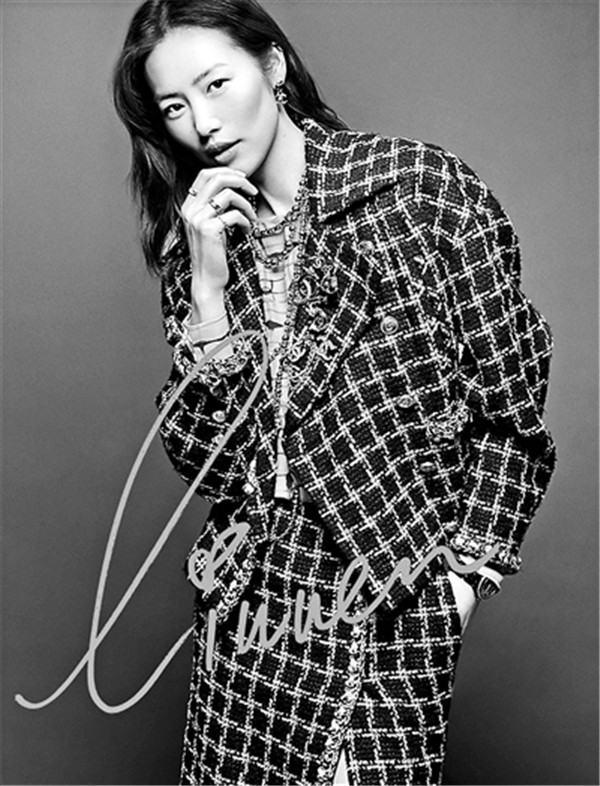
评论专区